《蜻蜓眼》无疑是我个人创作史上的一部很重要的书。
三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故事。我将与它的相遇看成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看成是天意—命运之神眷顾我,让我与它相遇。当初,一接触它时,我就已经知道它的宝贵,“价值连城”四字就在心头轰然作响。我很清楚,作为一个写故事的人,一个作家,他遇到了什么。但即使在“榨干”了故事主人对这个故事的记忆之后,我依然没有产生将它很快付诸文字的念头。
我是一个喜欢珍藏故事的人,而对那些可遇不可求的故事,更会在心中深深地珍藏着。藏着,一藏三十多年,就是不肯让它面世。感情上是舍不得(那种感情十分类似于一个父亲不想让他心爱的女儿出嫁),理性上我知道,一个作家必须学会对故事的珍藏。这是一个本领—珍藏的本领。珍藏的好处是:那故事并非是一块玉—玉就是玉,几十年后,甚至几百年后,它还是那块玉,而故事却会在苍茫的记忆的原野上生长。岁月的阳光,经验的风雨,知识的甘露,会无声地照拂它,滋养它。它一直在生长,如同一棵树,渐渐变得枝繁叶茂,直至浓荫匝地。三十多年间,有时我会想到它—想到它时,我就会打开记忆之门去看看它,更准确的说法是观赏它。我发现,我观赏的目光正在由平视逐步抬高,而改为仰视,不断抬高的仰视。我知道,那棵树,在长高。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会长成参天大树。终于有一天,这棵树不再是树,而从植物变成了动物。这个健壮的动物,不再安于在记忆的原野上走动,它要去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任何栅栏都不能再阻拦它。沉睡,哈欠,继续沉睡,一跃而起,精气神十足,它一定要走出记忆之门,到光天化日之下。“放它出来,到大世界去!”我听从了这一似乎来自天庭的声音。
于是,它就成了《蜻蜓眼》。
“蜻蜓眼”是一种宝物,是一种椭圆形的珠子。在小说中,它只有两枚。但我知道,现在它就不是两枚了。一册《蜻蜓眼》就是一枚。它将繁衍成多少枚呢?我想不是谁都能说出这个数的。
挨着“珍藏”这个字眼的是“沉淀”这个字眼。回想三十多年的珍藏,冷静一想,我发现,其实不是故事在变,而是我在变。我的思想在变,我的审美在变,我的趣味在变,我的情感以及情感方式在变,我的目光在变。而这一切的“变”,都是往更可靠更成熟的方向去的。当时许多令我冲动的情节与细节,时过境迁,不再令我冲动,而归于平淡;而当时并不上心、觉得微不足道的情节和细节,反而在逼近我的目光,熠熠生辉。一些当初的见解在瓦解,而新的见解在生成。我感到,自己书写和驾驭整个故事的能力在一天天地增强,心虚在不断地被新生的力量削弱,代之而起的是满满的信心。前后比较,我觉得昨天对这个故事的领会与把握,跟今天对这个故事的领会与把握,有天壤之别。
也许是我对故事反应迟钝,也许是我的“深思熟虑”,我通常的状态就是这样:很难做到逮到一个故事马上就将它变为文字。我写了这么多年作品,还很少发生过早晨刚得到一个故事,晚上就立即将它转换成文字的事情。通常,我不善于写当下,而只善于写过去。但我自认为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并且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写今天早晨发生的事和今天早晨听到的事。
像“蜻蜓眼”这样的故事,我只能取端庄的写作姿态,用庄重的语调去书写。事实上,我的写作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姿态,这样一种语调。我不太善于也不喜欢—甚至说是很不喜欢那种油腔滑调的写作语调。我写过一些谐趣的文字,如“我的儿子皮卡”系列、“笨笨驴”系列、“萌萌鸟”系列,但我将这样的笔调理解为谐趣或幽默。其实,我一直很喜欢谐趣和幽默。这种喜欢一样体现在端庄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火印》等作品中。但我是将这种谐趣和幽默归入“智慧”这种境界的。在写作倾向上,我可能更赞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写作。那时的作家,姿态是端庄的,语调是庄重的。无论是雨果、巴尔扎克还是托尔斯泰、肖洛霍夫,也无论是鲁迅还是沈从文,他们的姿态与语调都是如此。即使讽刺,姿态也是端庄的,语调也是庄重的。在《巴黎圣母院》中,在《高老头》中,在《战争与和平》中,在《静静的顿河》中,在《呐喊》《彷徨》中,在《边城》中,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他们的姿态和语调。但随着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动以及泛滥,这种姿态与语调被冷落了,直至被嘲笑与否决了,代之而起的是黑色的、冰冷的、讥讽的、嬉皮笑脸的或是自虐式的嘲讽,仿佛整个世界无恶不作、荒谬绝伦,不配以端庄的姿态面对,不配用庄重的语调叙述。当年朱光潜先生在区别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时,说西方美学追求的是“崇高”,中国美学追求的是“秀美”。而如今,无论是崇高还是秀美,都几乎消失;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西方文学,都统一到了阴冷的、令人叹息和无望的谐谑上。崇高、秀美几成明日黄花。
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被无情地否定了。这个世界没有正义,没有善良,没有美好,有的只是阴险、无聊、萎靡不振、蝇营狗苟、变态……然而,这个世界真的就完全如此吗?其实,我们的头顶总有灿烂的阳光;许多时间里,月色迷人,星空下总有夜曲在远处响起;爱情无处不在,博大的母爱、父爱常常让我们心头流淌暖流;春天里百花齐放,秋天里更是色彩斑斓;而当冬季来临,白雪皑皑的世界,使人感到一片纯洁和冷静……其实,那些拒绝端庄、庄重的作家,他们一直享受着这个世界给他们的种种远超普通百姓的好处。喝着咖啡或葡萄酒,在舒适的空间里自由地驾驭文字,荣誉、金钱,他们往往应有尽有。但他们就为那份虚拟的“深刻”,将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统统过滤掉,而只留下一堆黑色的渣滓。然后,便开始令人绝望的谐谑。如果他们说文学的端庄、庄重乃是虚假,那么他们的这般姿态就一定是诚实的吗?
我不相信我取端庄的姿态用庄重的语调来讲“蜻蜓眼”的故事,就一定无法深刻—即使真的无法深刻,我也不想改变这种姿态与语调。
做人要做一个聪明人,做作家也得做一个聪明的作家。不是他真聪明,而是他想着自己要聪明。这么想着—必须这么想着。这么想着,说不定他会真的聪明起来。
我想,这份聪明首先表现在他知道将什么视为他的写作资源,知道他的双足是站在哪块土地上的—生他养他的土地。忽视、忘却甚至拒绝这块土地,是愚蠢的、不聪明的,很不聪明。因为,那块土地在星辰转换之中,早就铸就了他的精神,他的趣味。忽视它,忘却它,拒绝它,将会使他变得一无所有,甚至导致文学生命的死亡。关键是,这块土地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生长故事—人类社会所独有的故事—独有的品质,独有的发生方式、演进方式以及独有的落幕方式。我看到了这一资源—汪洋大海般的资源。常常,我会为选择了其中的一个大故事而欣喜若狂。我知道那个故事会给我带来什么—带来荣耀,带来幸福,带来来自世界的目光。
但只知道坚定地立足于这块土地的人,仍算不上最聪明的人。最聪明的人是双足坚定地立于这块土地,而眼睛却穿过滚滚烟云去眺望天地连接之处,眺望国家界碑之外的广阔世界的人。目光永远比双足走得更远,而心灵则能走得更远。这个人,这个愿意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人,懂得一个关乎文学性命的道理,这就是:生他养他的土地,是他写作的永恒资源,而他思考的问题是世界的;题材是中国的,主题是人类的。他要从一个个想象力无法创造出的中国故事中,看到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他要从一个个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之中,看到千古不变的基本人性,而他又永远希望用他的文字为读者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
我一直想做这样一个聪明人,《蜻蜓眼》也许充分显示了我的真诚愿望。
解读四个成语
这四个成语可能与文学有关,与文学的生命有关。它们分别是:“无中生有”“故弄玄虚”“坐井观天”和“无所事事”。
无中生有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能力是文学的基本能力。也可以说,无中生有应是文学所终身不渝地追求的一种境界。
由于无止境的精神欲求和永无止境的创造的生命冲动,今天人类已经拥有一个极为庞大的、丰富的、灿烂辉煌的精神世界—第二世界。上帝创造第一世界,而人类创造第二世界。这不是一个事实的世界,而是一个无限可能的空白世界。创造什么,并不是必然的,而是自由的。我们要丢下造物主写的文章去写另一篇完全出自于我们之手的文章。上帝是造物者,我们就是“准造物者”。我们眼前的世界,既不是造物主所给予的高山河流、村庄田野,也不是喧嚣的人世,而只是一片白色的虚空,是“无”。但我们要让这白色的虚空生长出物象与故事—这些物象与故事实际上是生长在我们无边的心野上。
我们可以对造物主说:你写你的文章,我写我的文章。
空虚、无,就像一堵白墙—一堵高不见顶、长不见边的白墙。我们把无穷无尽、精彩绝伦、不可思议的心象,涂抹到了这堵永不会剥落、倒塌的白墙上。现如今,这堵白墙已经斑斓多彩,美不胜收,上面有天堂与地狱的景象……这个世界已变成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个世界不是归纳出来的,而是猜想演绎的结果。它是新的神话,也可能是预言。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予一切可能性以形态。这个世界的唯一缺憾就是它与我们的物质世界无法交汇,而只能进入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双足无法踏入,但我们的灵魂却可完全融入其间。它无法被验证,但我们却又坚信不疑。
无中生有就是编织,就是撒谎。
劳伦斯反复说:“艺术家是个说谎的该死家伙,但是他的艺术,如果确是艺术,会把他那个时代的真相告诉你。”而这一思想的最富个性的表述是由纳博科夫完成的:“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跟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因为撒谎次数太多,最后真的被狼吃掉了纯属偶然,而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在丛生的野草中的狼和夸张的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副棱镜,这就是文学的艺术手段……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艺术的魔力在于孩子有意捏造出来的那只狼身上,也就是他对狼的幻觉;于是他的恶作剧就构成了一篇成功的故事。他终于被狼吃了,从此,坐在篝火旁边讲这个故事,就带上了一层警世危言的色彩。但那个孩子是小魔法师,是发明家。”
写作者应该是那个放羊的孩子。
故弄玄虚
要体会这个成语,可以回味一下两个早被谈得起了老茧的作家: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
博尔赫斯的视角永远是出人预料的。他一生中,从未选择过大众的视角。当人们人头攒动地挤向一处,去共视同一景观时,他总是闪在一个冷僻的、无人问津的角度,用那双视力单薄的眼睛去凝视另样的景观。他去看别人不看的,看出别人看不出的。他总有他自己的一套—一套观察方式、一套理念、一套词汇、一套主题……
这个后来双目失明的老者,他坐在那把椅子上所进行的是玄想。
他对一切都进行玄想—玄想的结果是一切都不再是我们这些俗人眼中的物象。
我同意这种说法,博尔赫斯的作品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而另一个写成年童话的作家卡尔维诺,更值得我们去注意。他每写一部作品,几乎都要处心积虑地搞些名堂,这些名堂完全出乎人的预料,并且意味深长。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位作家像他那样一生不知疲倦地搞出一些人们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名堂。他把我们带入一个似乎莫须有的世界。这个世界十分怪异,以至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总会有一种疑问:在我们通常所见的状态背后,究竟还有没有一个隐秘的世界?这个世界另有逻辑,另有一套运动方式,另有自己的语言?
“世界正在变成石头。”卡尔维诺说,世界正在“石头化”。我们不能将石头化的世界搬进我们的作品。我们无力搬动。文学家不是比力气,而是比潇洒,比智慧。面对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的玄想—故弄玄虚,我们是否应该得到一些启发:中国文学应该如何启动自己关注一些玄虚的问题—形而上的问题的功能?
坐井观天
我们假设,这个坐井者是个智者,他将会看到什么?坐井观天,至少是一个新鲜的、常人不可选择的观察角度,并且是一种独特的方式,而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向我们提供另一番观察的滋味与另样的结果。
什么叫文学?
文学就是一种用来书写个人经验的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那个作家在创作时尊重了自己的个人经验、是以个人的感受为原则的,那么他在实质上就不能不是坐井观天的。
“每个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会得到不同的经验。”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许多年前,一个打工的女孩经常来北大听我的讲座,她告诉我,她小时候在冬天的晚上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帮家里洗碗。我觉得这太奇怪了。洗碗是很多人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所以才发明了洗碗机嘛。她解释道,小时候家里很穷,穷到连几分钱一盒的蛤蜊油都买不起,于是,她想通过洗碗在干燥的手背上找到一点点油腻的感觉。我敢断言,这种经验是她个人所独有的。
我们没有理由不在意我们自身的经验。我们应当将自己的作品建立在自己的经验的基础上。经验是无法丢失的前提。
《红瓦》刚出来的时候,一位批评家指出,他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写“文化大革命”。因为在此之前,作家一涉及“文化大革命”,都在写集体性的记忆:戴帽子游街、批斗、蹲牛棚。但其实,不同人的“文化大革命”是不一样的。《红瓦》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但绝不是现在一般作品中所记忆的集体性的“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才十一岁,刚上中学。我的父亲把我交给一个女语文老师。她领着我们一群孩子过长江到上海去串联,路途要经过苏北小城南通。当时,我的感觉是:整个世界沦陷坍塌了,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南通。因为人流滚滚,我们小孩子经常被挤丢,老师为此很着急,用张艺谋的电影来讲,“一个都不能少”。她经常是找到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又丢了,非常紧张。于是,她在街头给我们每个小孩买了一个玩具。那是一种用塑料做的鸟,灌上水,鸟尾巴上有一小眼,嘴对着小眼一吹,水就在里面跳动,会发出一种欢鸣的声音。她告诉我们,如果谁掉队了,就站着别动,吹水鸟,她就会循着声音找谁。这样的效果很好。当时,男孩女孩全拿着一只水鸟一路走在南通小城,那真是南通小城的一道风景线。
后来,我们这个串联小分队得到了一张集体船票,准备坐东方红一号到上海。码头上人山人海,非常混乱。老师知道把一个队伍完整保持到船上,根本不可能。于是,她让大家上船以后在大烟囱下集合。队伍哗地一声散掉了,大家各奔东西。我开始拼命吹水鸟,但是没有一个人呼应我。我很焦急。吹了很久,远处终于有一个人呼应我,我当时的心情不知道有多么激动,就像一个地下党员跟组织接头,接了好久没接上,现在终于接上了。然后,我吹一个长声,他也吹一个长声;我吹一个短声,他也吹一个短声;我吹一长一短,他也吹一长一短—像两只小鸟在一起合鸣。
后来,我上了船,到了大烟囱下,却发现没有我的老师和同学。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东方红一号缓缓离开江岸,向江心开去。我到处找大家,不停地吹水鸟,吹得嘴唇都麻木了。最后回到大烟囱下,依然没有一个人。这时,我知道了,今天上了船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一个十一岁的只去过县城两三次的小男孩,在秋天的黄昏,一个人在长江之上,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心情?当然,他是非常悲哀的。我印象很深,我当时趴在栏杆上哭,不是那种悲愤的号啕大哭,好像哭声中还带着一种甜丝丝的感觉。看着眼泪随着风儿飘忽摇摆,我觉得很好玩,就再哭;哭累了,就在大烟囱下睡着了。睡到深夜,模模糊糊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了,就拿起水鸟接着吹。这时,隐隐约约觉得一个苍茫的地方有人用水鸟呼应我。我怀疑这是幻觉,摸摸头上的帽子,再摸摸身边的行李,确信这是真的,于是便拼命地一边吹一边往船尾跑,那个人也拼命向我这里跑。最后,我们会合了。在灰暗的灯光下,我看到竟是一个女同学,而且,最让人尴尬的是:那个女孩是自从我上初中以后全班同学拿她和我开玩笑的那个女孩……
这就是我的“文化大革命”。
文学必须回到个人的经验上来。
一个小说家自己的鲜活感觉大概永远是最重要的。
无所事事
卧病在床的普鲁斯特留给我们“无所事事”的印象,而“无所事事”恰恰可能是文学写作所需要的上佳状态。由无所事事的心理状态而写成的看似无所事事而实在有所事事的作品,在时间的淘汰下,最终反而突兀在文学的原野上。
中国文坛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家,也少有无所事事的作品。我们太紧张了。我们总是被沉重的念头压着。我们不恰当地看待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将文学与社会紧紧捆绑在一起,对当下的社会问题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普鲁斯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启发。他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之下,发现了许多奇妙的东西,比如说姿势—姿势与人的思维、与人物的心理,等等。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他用了许多文字写人在不同姿势之下会对时间产生微妙的不同的感觉:当身体处于此种姿势时,可能会回忆起十几年前的情景;而当身体处于彼种姿势时,就可能在那一刻回到儿时。“饭后靠在扶手椅上打盹儿,那姿势同睡眠时的姿势相去甚远……”他发现姿势奥妙无穷:姿势既可能会引起感觉上的变异,又可能是某种心绪、某种性格的流露。因此,普鲁斯特养成了一个喜欢分析人姿势的习惯。当别人去注意一个人在大厅中所发表的观点与理论时,普鲁斯特关闭了听觉,只是去注意那个人的姿势。他发现格朗丹进进出出时总是快步如飞,就连出入沙龙也是如此。原来此公长期好光顾花街柳巷,但又总怕人看到,因此养成了这样步履匆匆的习惯。
人在无所事事的佳境,要么就爱琢磨非常细小的问题,比如枕头的问题、姿势的问题、家具的问题,要么就爱思考一些大如天地的、十分抽象的问题。这些问题自有人类历史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被追问,是一些十分形而上的问题。在普鲁斯特这里,他是将这些细小如尘埃的问题与宏大如天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的—在那些细小的物象背后,他看到了永世不衰、万古长青的问题。
作家也是知识分子,但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他既需要具备一般知识分子的品质,同时又需要与一般知识分子明确区别开来。作为知识分子,他有责任注视“当下”。面对眼前的社会景观,他必须发言,必须评说与判断。“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被规定为:他必须时刻准备投入“当下”。当一个知识分子对他所处的环境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竟然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时,他就已经放弃了对“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坚守。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知识分子永远是强劲的驱动力。
然而,当他在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种—作家时,他则应该换上另一种思维方式。他首先必须明白,他要干的活儿,是一种特别的活儿。作家所关心的“当下”应含有“过去”与“将来”。他并不回避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跨越时空的:过去存在着,当下存在着,将来仍然会存在着。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此刻,那些琐碎的、有一定时间性和地域性的事物在他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他可以视而不见,而看到的是—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讲,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
“写小说应该写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米兰•昆德拉说得千真万确。

一个小说家自己的鲜活感觉大概永远是最重要的
胡爱林 2018-06-20 10:0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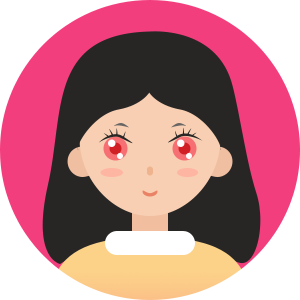
好想在这里发布作品不知道能不能审核通过。
曾艳萍 2018-12-24 14:06
曹文轩的《蜻蜓眼》创作谈,我很喜欢 ,这篇评论字字珠玑,发自肺腑,读了之后让人受益匪浅,对个人的写作非常有帮助。 曹文轩是我非常喜爱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我读过好几部,虽然是儿童文学作品,但好多成年人也喜欢阅读,他描写的水世界太精彩了,是流动的生命之水给了他写作的灵感,是珍藏心中多年的故事长成了参天大树,最后这棵树由动物变成了植物,成了他手中的绝妙佳作。 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爱一个人的作品是因为读懂了作者,我常常在心中想象曹文轩老师坐在窗前,握笔沉思,继而挥笔书写着心中那沉淀已久的一个个鲜活的故事,那些精彩的故事滋润着一代代儿童的心田,让他们获得了宝贵的精神食粮,从而健健康康地成长。感谢曹文轩老师为儿童读者的付出,祝曹老师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不好意思,家里来客人了,
占正帮 2019-02-21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