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这是一首久远的歌曲,名字叫做《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熟悉的旋律,亲切的声音,留下的是美好记忆。若我年纪不相上下上世纪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出生的人,《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耳熟能详。儿时,听着这首歌,感觉如小松树般茁壮地成长,快快地长大成材。成长的记忆,总是烙下许多深刻并亲切的印记。
今岁,又逢秋季。在江汉平原的家乡,走出小城,几乎短促的时间,便可见闾巷草野,再不远远便可看到广袤的稻田。丰收时节的稻田里,景致浓郁得熏熏醉人,可邀来画家、摄影家们作画拍摄,几乎不用细阅慢品,信手拈来便可成为艺术品的。被秋收深深地震撼过,更在秋收里感悟内心的踏实,偶得闲暇驻足稻田旁,除去映入眼帘无垠的黄灿颜色,若拾起一串稻穗掂量掂量,感觉手心里,沉甸甸地收获了。几分失落,已难觅一垛又一垛的谷堆,还有太阳照在谷堆上谷堆后儿时嬉戏的影子。扪心自问:忘却谷堆,还有何种资格把自己视作农民的后代么?还有,在无数次丰年稔岁的秋天里,无数次地漠视了谷堆。这么多年,社会阔步迈进着,农业生产长足发展,机械化作业收割稻谷几近颗粒归仓。过往云烟般的谷堆,仿佛早已完结历史使命,划归“非物质状态”。
“谷垛码起来,集体大丰收,我们吃得饱”。在秋天里惦念起自己儿时的谷堆,心理因素是后怕重新过上缺衣少食的日子。 那时,每每秋收总会有“双抢”,参加“双抢”的“男劳力”、“女劳力”们,卯足干劲,不叫苦、不叫累,挥汗如雨,轰轰烈烈,兴高采烈地庆祝着收获。透过不同的途径,在不同的场合,获悉当时农业生产的断续信息,通过叠加做出了一个盲目的臆断:当时的谷堆,的确还是承载了不少东西的,特别我的前辈的农民们,在秋收季节展现出来的表情与内心的真实想法,是有一定差异的。
解放后,分田到户让所有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取得身份与地位翻身得解放, 与“地富反坏右”们区分了阶级区别了地位,为了农业生产,兴水利、挑泥巴、筑梯田、挖水沟、防汛抗旱、砍树割草。大跃进时,谷堆寄托了农民美好愿景,象征着农民翻身解放,成为革命事业成功的标志。谷堆的地位水涨船高分量千钧,在反复的升华与持续的神话里,谷堆堆码的速度势不可挡,数据累创新高,亩产万斤、几万斤甚至到了十万斤。有一张老旧的照片,留下那个时代的特殊影像:“丰收了”的农民们,站在高高的谷堆上,呵呵地开心地笑着;而高高的谷堆,则托举起农民们甜蜜的梦。泡沫里的幸福,来得迅猛,走得更是令所有人猝不及防,演绎为苦涩的梦。
一篇短文,详实披露“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发生于某地农村的一起盗窃案件:某生产小队的小队长,不忍心看着村民饿得面黄肌瘦甚至活活被饿死,与人一合计趁着风黑夜高之夜,偷偷地从谷堆上拉下若干捆稻谷,私自分给队里每家每户,不久便遭人检举揭发东窗事发,小队长被五花大绑押到县里,判了徒刑进了大牢。这起陈年旧案,至今看来还有几分煽情与悲情。
下乡,驾车路过在那个年月被围垦的湿地,同行的一位老同事,曾亲自参与了当年的围湖造田运动。据他介绍:我们车轮子下的道路,是上世纪七零年代初,由包括他在内的数万民工,花了几年的时间,肩挑背扛出来。秋收完毕,大大小小水利工程的工地上人声鼎沸,各级领导亲自督阵,水利工程指挥部的大广播高高架在树上,反复播送着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我们战天斗地的口号,大大小小的黑板上,帖满《决心书》、《挑战书》,一些则是民工们咬破手指写就的血书。所有的人都坚信,围垦为了来年来日的丰收,可以收获更多的谷堆。围垦的号令,挖掘出农民潜能,迸发出农民豪情,凝聚成一种义无反顾战天斗地的壮志,为了谷堆!为了荣耀!围垦得到的回报,是最新最大的收获,若遇荒年灾年,也多多少少收获了。圆形,椭圆形,圆锥型的谷堆;长方形,正方形的谷堆;一大堆,一小堆的谷堆;几万斤,几千斤的谷堆;祖国各地,天南海北的谷堆;一季稻,两季稻,三季稻的谷堆;增收了,减产了的谷堆。所有的谷堆,耸立在所有农民心里,被敬仰和景仰。
曾做过农民的老同事还说:那时候,打心里感谢谷堆,尤其是谷堆留下的稻草,睡觉铺垫稻草可以遮风挡雨,挑泥巴踩踏稻草不会陷入沼泽。老同事所在的生产大队,在水里工程进度上遥遥领先,得了第一名,指挥部特地下拨了一些大米猪肉,犒劳水利尖兵。这是一顿令人拙舌的晚餐,只有十五六岁的他,一口气吃下一斤二两的大米饭和两斤米粉蒸肉。为何能食量惊人,因为那是一次庆祝胜利的晚餐,也可能因为是有饥饿的原因吧。
自己的记忆,再次穿越到自己儿时生活过的农场。农场仓库前,有约莫三四百平方的禾场。禾场与农场宿舍地基,是一样的夯土,是一样的扎实。禾场上,每至秋收的时节,便会耸立起三五个谷堆。与我一般大小的伙伴们,其顽皮无知到什么程度,该用什么词来形容?稍加思索,找到多年前的一条农药广告比较恰当: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当时看来,顽童们为所欲为嬉戏,极可能在瞬间里转换成破坏生产的事情,而在当时一切破坏生产的行为,都是恶积祸盈,甚至祸害滔天。譬如,顽童们玩玻璃弹珠挖洞穴,会搞得禾场凸凹不平,影响谷穗脱粒与晾晒;更有顽童置“防火防特,人人有责”口号于不顾,在禾场上划火柴闹出火险,便是纵火。清晰地记得,自己六岁那年的秋收,田里的谷捆子还没全部运回,农场领导喝令所有人停止了劳动,在禾场的谷堆旁召开紧急大会。原来,农场会记抽屉被撬,被人偷走少量现金、饭菜票与粮票,应该是家贼趁农忙而下手。农场领导说:先琢磨人的问题,再琢磨秋收的问题;谷子可以不收,家贼一定要捉。会议持续开了大约上十天,不分白天黑夜地开会,所有人风兵草甲人人自危,先是极力地辩白洗清自己,后来便是积极举报相互揭发。最终,强大的政策攻势瓦解了家贼的心理防线,家贼主动坦白交待悉数交出赃物。据说,当年农场的粮食生产滑坡减收,上级肯定了农场“抓革命促生产”的做法。
当今全世界最权威的农业组织——联合国粮农署,认同了一桩事实,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先生在水稻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解决了困扰国人多年的“吃饭问题”,其“杀手锏”即是尊重科学、尊敬生命、遵循自然规律。不知道,我们该是鸣谢袁隆平,还是该铭记袁隆平。再大的谷堆,再高的谷堆,囤了再多的物质状态下的粮食,也会被吃得精光颗粒不剩。
一个国家与民族,当有些勇气的,囤积并留存下精神状态的谷堆,只有值得骄傲的精神才是传世的食量,承载着文化,传承着文明。要不然,我们这一顿吃得撑破肚子,也将会被饿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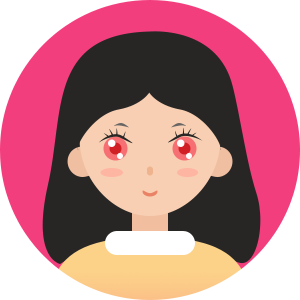
我几乎不记得粮票是什么样子,也不记得有没有见过粮票,也许见过,忘记了吧。小时候粮食应该是不够吃的,但我十岁之前,从来不知道饿是怎么回事。听母亲说,父亲会在分粮食的时候,偷偷多拿些,或者,夜晚去找些杂粮。记得有一年夏天的夜晚,屋外雷电交加,母亲说父亲去挖藕去了,她担心的倚靠在框上,口中念叨着:这么大的雨,这么大的雷,找不到就回来撒。 一条闪电横过,震耳欲聋的雷声像要炸开天空,母亲本能的后退了几步,我看到她在哭,我和弟弟也哭起来。这是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幕。 父亲总能找到食物,母亲总是把那些食物做得很可口,因此我们姐弟三个基本上没有饿过。和我同年的,一提起过去,就说有多苦,我却是没有感受的。
冷月雕栏 2018-07-03 22:56